| 爱民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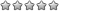
等级: 城镇农民 城镇农民
贴子:56
积分:132
元:0
注册:2007-06-04 |
|
|
|
      |
第 1 楼 |
|
 腹有博学怀若谷 身兼多艺德如兰 腹有博学怀若谷 身兼多艺德如兰 |
初识张滃先生时,正是雨雪霏霏。那是今年元旦,张先生在大同市展览馆举办个人画展时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再见张滃先生时,已是杨柳依依,今年五一黄金周前,接到报社的任务,在张先生的办公室我采访了他。
对张滃先生,我不知该称他什么家好,那头衔多得让人看着眼花。他是原大同市美术设计院院长兼总设计师,原大同市规划局副局长。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山西分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曾任大同市美协副主席;中国室内建筑师学会会员;大同市建筑装饰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大同市城市规划协会长;大同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大同市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大同市政府专家顾问组专家;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等。一般人一生一世,专一门,精一业已是很了不得,但张滃先生则以一己之力,广涉多门,精研多业,蔚然而成大家,不由使人心中充满敬仰之意。带着敬仰之情,倾听着先生的讲述,我走进了先生的故事里。
书香门第一才童,大学礼堂露峥嵘
张滃先生是土生土长的老大同人,一九四四年出生在城内马王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张霭堂乃一代儒商,解放前就是大同老字号绸缎庄“云锦章”的总经理。母亲也是颇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经营生意之暇,其父每天都要看书练字,尤其在写字方面下过很大功夫。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父就是大同著名书法家,当时的“人民大礼堂”、“九龙电影院”、“大同市人民委员会”、“大同市图书馆”、“大同二中”等牌匾题额,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张老先生还是大同市第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常常教育孩子们:“艺好不好性好”,激励孩子们从小重视学问品德的修养。张滃的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操持三十多人的大家庭生计,调理的井井有条。父亲的良好品格和教养,也给张滃兄弟们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地作用。张滃从小就十分聪明、活泼、兴趣广泛。大哥张,二哥张沏,他们不仅品学兼优,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各有专长,张的小提琴演奏在当时全市青少年中名列前茅,张沏的诗歌、文章都写得很好,深得师生好评。张滃在两位哥哥的影响下,对文学艺术还真下了些功夫。转眼到了中学毕业,张滃顺利地考入了山西艺术学院,主攻美术专业。1959——1962年的四年间,张滃在这里学习深造,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展露的机会,那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元旦晚会上,张滃作为一名美术专业的学生,却登台表演了笛子独奏《放风筝》。只见大幕拉开,一位十五六岁的风华少年,翩然走上舞台,竹笛一横,涌出一串串悦耳动听的音符,展现出一个生趣盎然的画面:一群少男少女,在那花红柳绿的阳春三月,拎着自制的风筝踏青而来。他们笑着、跑着,风筝在天空中渐渐地升起来,越升越高,他们的歌声、笑声也随着风在空中飘荡,越飘越远……一曲终了,掌声雷动。是啊,一位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却有如此的音乐天赋,如此精彩的演奏技巧,怎么能不令他们惊叹和折服呢?!也就是从那时起,张滃成了山西艺术学院的名人、明星,他的表演或演奏成了学校组织晚会活动的保留节目。
精研规划成专家 名城保护建新功
张滃先生告诉我,他是学美术专业的。但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专业却变成了业余。1962年他从山西艺术学院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山西省文化厅工作,后又到山西省二轻厅、大同化纤厂工作。1973年调大同市展览馆,后又调到市政府办公厅。1984年筹建大同市美术设计院,任院长兼总设计师。1989年兼任大同市规划处副处长。1998年至2001年因当时的规划局长患病不能工作,张滃又以规划局第一副局长的身份主持了三年规划工作。规划是一项专门的学问,与美术专业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张滃就是张滃,他要么不应承,一旦应承下来,就一定要干好干精。凭着担任规划局副局长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凭着他不耻下问、勤学不厌的精神,他很快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在他主持规划工作的几年中,我市规划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进步。他主持参与了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大同市城市建设控制性详细规划;古城保护规划;红旗广场、火车站广场整治规划;新世纪广场规划;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各县县城总体规划等。此外,他的论文《中规中矩 保护发展》、《城市规划是城市宏观环境艺术》、《个性——一个永恒的主题》等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加上发表在省市级刊物上的规划方面的论文总计有几十篇。他还作为云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组的专家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在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张滃还担任了我市第十、十一两届政协委员,作为大同市城市规划和名城保护的专家,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在大同市的城市形象建设、文化宣传、名城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提案和建议。为提高大同的城市品质,推动大同经济振兴发挥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能诗、能画、能作曲,博学深研艺方精
在行政工作之余,张滃总在广阔的艺术海洋中荡舟远行,他挤出一点一滴的时间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学习中外绘画艺术知识,学习音乐作曲,学习摄影技术,学习书法篆刻,学习工艺美术的设计。对这些众多的艺术门类他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和激情。哲人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情是澎湃的动力。因此对一门技艺或学问别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的,张滃则只用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学懂弄通。有些东西他还可以无师自通,比如对中国古典诗词,他坚持不懈的自学,打下了坚实的诗词根基。他不仅熟悉古诗词的平仄韵律,而且能从中悟出其所包含的丰富意境,这为他后来绘画技术和其他技艺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艺术灵感的触发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他的诗词功底也从他主办的《大同城市规划》每期发刊词中可见一斑。再如对音乐,张滃从小就喜欢,上大学时学习专业之余他忙里偷闲听了不少音乐课,也看了不少音乐书。毕业时,他这个专业的学生,音乐知识和才能比一般音乐专业的学生也毫不逊色。他能作曲,,还能搞二胡,长笛、笛子,小提琴等多种器乐演奏,甚至还能当乐队指挥这些角色行当在山西省二轻文工团和大同化纤厂文工团他都当过。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有二胡协奏曲《丰收的喜悦》、板胡独奏曲《赶路》等。他创作的歌曲有《春之歌》(女声二重唱)、合唱组曲《会战凯歌》等,这些作品都在他所在的文工团演出过。1997年香港回归,一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张滃激情难抑,热血沸腾,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五星红旗下的紫荆花》(男声独唱),发展在大同日报上。
工艺美术方面张滃也有不小的成就。1984年起他任美术设计院院长,又兼总设计师,多年来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在他的团结带领下,大家在干中学,学中干,不断提高,不断前进,很快就打开了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同市街头灯箱广告就是他们的创意和杰作。后来他们又向城市雕塑、大型壁画发展。张滃先生自己独立创作的大型壁画有大同火车站的《福地宝城》,大型雕塑有红旗广场“福地宝城”(俗称三把刀)。他主持并参与创作的大型壁画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愉快的旅行》、《太阳石的传说》、《长城颂》,这些作品对大同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大同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并主持了许多大型雕塑的创作,如青磁窑煤矿的《初升的太阳》、云冈宾馆的《天歌》、大同公园的《镇河牛的传说》等这些作品,成为大同城市文化的象征。此外,张滃的书法、摄影等也都很有成就。在书法方面真草隶篆,广泛涉猎,尤擅行草,一笔浩然。摄影方面,市内许多大型的展览他既是展厅设计者,也兼摄影,不少作品即出自他手,从构图到用光,从选取角度到暗房技术,他都技艺娴熟。
“艺术类相别,妙理皆相通”,在对众多艺术门类的实践过程中,也为张滃的绘画艺术奠定了宽厚而敦实的基础。这些艺术尤如金字塔的底座,它把张滃的绘画艺术托向塔尖。在众多艺术中,美术绘画是张滃最擅长,最喜爱的艺术。在水墨丹青、七彩画卷之中,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和感情。因此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我看过他2007年元月在大同展览馆展出的作品,从其总体风格来看,确是大手笔,大气派。如《武周遗韵》以大背景、小主体的构图方式,配以森版宋体文字说明,既映衬出云冈石窟的历史沧桑,又寓喜着云冈石窟艺术保护和发展的任重道远。如《华彩乐章》以五线谱为主体图形,点上红蓝绿等各色,把时间艺术用空间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颇有装饰画的韵味,构思创意十分精巧。如《喝彩》以红掌花喻手掌,红花衬金蕊,无声胜有声,既有深刻的寓意,又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作品中还有不少诗配画,画配诗的佳作,如松竹梅兰组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再加上或潇洒、或圆润、或端庄或古朴的书法题记,更显得高雅脱俗。总之张滃的美术绘画风格给人的感觉是,题材广泛,构思深邃,形象生动。色彩鲜明,笔力雄浑,意味悠长,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他的绘画作品有不少发表国家和省一级刊物或美展上。如宣传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吸烟有害健康》等年画、版画、国画也有不少作品入选国家省市各级展览。改革开放以来,张滃的画作还有不少为外国友人购买收藏,张滃以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博采众艺的功力,熔铸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淡薄名利尚宽容,快乐潇洒不老翁
我曾接触过张滃的不少同事和朋友,大家对张先生的为人一言一蔽之:“为官是好官,做人是好人”。张先生身材魁悟,面相和善,一脸慈祥,待人接物,自带春风,蔼然一付长者风度。他说:“自己从省里到市里,大大小小待过不少单位,担任过不少职务,但从未与人吵过闹过,他与所有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当美术设计院长和规划处、规划局副职时,也从没有把“官”和“权”当回事,更没有去以“官”谋利,以权谋私。他很欣赏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也时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美术设计院,他求贤若渴,待人如亲。对犯了过错,或有缺点的人,他也给予善意的帮助和宽容。他工作中身先士卒,艺术上实行民主,把一个面向市场、自收自支、一穷二白的事业单位,搞得是人和业兴,欣欣向荣。在他主持规划局工作期间,也曾有人劝他,“老局长病了几年,上班的可能性不大,你找找领导,走走门子,由副转正,水到渠成。”他都婉言谢绝了。有人讥讽他傻,但他心中却十分坦然。官位权柄不贪恋,名利锁难缠身,张滃一生最爱是艺术,最贵是超然。2004年,张先生年满花甲,本该退休安享晚年,却因人缘好,业务精,又勤快,而被单位返聘,每天照常上班。同时还依然担负着历史名城保护专家组副组长、城乡规划协会协会长、政府专家组专家等社会头衔。但快乐潇洒天性使然,也总在忙碌中偷得一些闲暇,写字、绘画、篆刻、弹琴、唱歌。节假期间,而他总是与老伴一起旅游,到名山大川,饱览胜景,积累素材。遇到双休日也时不时潇洒走一回,与老伴一起去北京看一场画展,听一场高雅的音乐会,从中感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
总之,求学以博、研艺以精,待人以宽,处事以和,心底无私,笑对人生,张滃就是这样一个快乐、潇洒的不老翁。
|
|
 |
|
|